贺卡是那种最普通的款式,封面印着一棵粗糙的圣诞树,金粉已经斑驳脱落。翻开来看,里面的字迹让我瞬间怔住了——那些字歪歪扭扭地爬在横线上,像刚学写字的孩子写的。“爸”字写得太开,像两个人背对背站着;“身体”的“体”少了一横;“快乐”的“快”写得东倒西歪,竖心旁和“快”分得太开,看上去像是两个字。
这是我父亲的字。那年我十二岁,他四十二。
记忆像被这些歪斜的字迹撬开了一条缝。那是1998年的冬天,父亲所在的工厂效益不好,他下岗后在家附近的菜市场租了个小摊位修自行车。每天天不亮就出门,晚上八九点才回来,一身机油味,指甲缝里总是黑的。
那年圣诞节前,班上的同学都在讨论要送什么礼物。我回家翻箱倒柜,只找到五块六毛钱。母亲在纺织厂上班,工资也不高,我不敢开口要钱买贺卡。正在发愁时,看见父亲修车摊上有个废弃的笔记本,牛皮纸封面,内页已经写满。我偷偷撕下最后一页空白纸,对折,用尺子比着,自己做了张贺卡。
封面画什么好呢?我想起父亲修车时专注的样子,便用铅笔细细地画了起来:一个男人蹲在自行车旁,手里拿着扳手,旁边散落着工具。画得并不好,比例有些失调,但能看出是在修车。我在旁边工工整整地写上:“祝爸爸圣诞快乐!”
父亲收到贺卡时,正在厨房洗他那双永远洗不干净的手。他擦干手,接过贺卡,翻来覆去看了很久。厨房的灯光昏暗,我看不清他的表情,只听见他轻轻“嗯”了一声,把贺卡小心地放在电视机顶上。
第二天放学回家,我看见父亲坐在饭桌前,面前摊着那张我手绘的贺卡,旁边放着从邻居家借来的新华字典。他握着笔——那支他用来记账的圆珠笔,手指因为常年用力拧螺丝而关节粗大,握笔的姿势很别扭,像在攥着一把扳手。
他写得很慢,每一笔都像在用力刻进去。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,偶尔写错一笔,就用透明胶带小心地粘掉重写。那专注的神情,比他修最复杂的变速车时还要认真。
“我在旁边偷偷看着,鼻子突然就酸了。”
后来我才知道,父亲只上到小学毕业就辍学帮家里干活了。爷爷早逝,作为长子,他十四岁就开始在建筑队搬砖。结婚后,为了多挣点钱,他什么活都干——工地、码头、后来进了工厂,从学徒做到技工。字,对他来说,是遥远而陌生的东西。
可就是这样一个人,为了给我回一张贺卡,查着字典,一笔一画地写了整整一个下午。
贺卡上的字虽然丑,内容却让我至今难忘:
“女儿,爸爸收到你的贺卡了,画得很好。爸爸没什么文化,但知道你孝顺。你要好好读书,将来做个有出息的人。爸爸修车不累,只要你过得好,爸爸就高兴。圣诞节带你去吃肯德基。”
落款是:“爱你的爸爸”。
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去肯德基。他坐在我对面,自己只点了一杯可乐,看着我吃汉堡、薯条、吮指原味鸡。店里循环播放着圣诞歌,玻璃窗外飘着南方少见的小雪。他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十元钱递给服务员,说再加一个草莓圣代。
“爸爸不吃,你吃。”他把圣代推到我面前,自己喝那杯快要见底的可乐。
如今我也做了母亲,女儿上小学三年级,字写得工工整整,偶尔还会嫌弃我签名的笔迹不够好看。每次看她坐在明亮的书房里写字,我就会想起那个冬天的下午,父亲笨拙地握着笔,在贺卡上留下那些歪歪扭扭的字。
那些字确实丑,横不平竖不直,结构松散,笔画生硬。可就是这样丑的字,却比任何书法家的作品都让我动容。每一个歪斜的笔画里,都藏着一个父亲全部的爱——那种不知如何表达,却愿意为你查字典、学写字的爱;那种自己舍不得吃一顿好的,却要省下钱来实现你小小愿望的爱。
这张贺卡我珍藏至今,每次搬家都第一个收好。现在它躺在一个透明的文件袋里,偶尔我会拿出来看看。女儿问这是什么,我说这是外公写给我的信。她歪着头看了半天,认真地说:“外公的字好像小虫在爬。”
我笑了,眼泪却忍不住流下来。
是啊,像小虫在爬。可就是这些笨拙的“小虫”,爬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光,爬过了生活的艰辛,爬进了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。
父亲老了,手抖得更厉害,已经写不了字了。去年他生病住院,我在病房陪夜,深夜听见他迷迷糊糊地说:“女儿,爸爸的字丑,你别嫌弃。”
我握着他布满老茧的手,贴在自己脸上。那双曾经能修好各种自行车的手,那双曾经笨拙地握着笔给我写贺卡的手,此刻虚弱地躺在我的掌心。
“不丑,爸爸,”我轻声说,“那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字。”
窗外的月光照进来,像那年肯德基店外的雪花。时光改变了太多东西,改变了容颜,改变了生活,改变了这个世界。但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——比如那张泛黄的贺卡上,歪歪扭扭却重如千钧的三个字:
“爱你的”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品易文章网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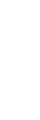 品易文章网
品易文章网
热门排行
阅读 (131)
1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21)
2扫码领洗发水,收到后是小瓶装阅读 (119)
3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9)
4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17)
5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