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3年春天,非典来了。学校封校,每天量体温,空气里都是消毒水的味道。四月的一个下午,他翻墙出校门——那时候出校要班主任批条,他为了出去,说是家里有急事。其实我知道,那天是我生日。
晚自习前他回来了,满头大汗,校服外套系在腰间。他隔着窗户向我招手,我假装去接水,在走廊的尽头遇见他。
“给你的。”他从裤兜里掏出个小盒子,塑料的,已经有点压痕。是个发夹,淡紫色的,做成蝴蝶形状,边缘有点粗糙,在当时的我们看来,却是顶漂亮的东西。
“现在商店都关门了,我跑了好几条街才找到还营业的。”他抹了把汗,“生日快乐。”
我攥着那个发夹,手心都是汗。那时候的感情多纯粹啊,一个发夹,一次翻墙,就觉得是一辈子了。
后来我天天戴着那个发夹。早读时别在刘海旁,体育课怕弄丢就小心收进笔袋,晚上回家取下来,还要用纸巾擦干净再放进抽屉。我妈笑我,一个五块钱的发夹,当宝贝似的。
高考后,他去了南方的大学,我留在北方。异地恋的日子,我们写信,攒电话卡,在QQ上聊天。每次视频,他都会说:“还戴着那个发夹呢?”我说是啊,戴习惯了。
其实发夹早就旧了。蝴蝶翅膀上的漆掉了一些,弹簧也不如以前紧,但我还是戴着。好像戴着它,就戴住了十六岁那个春天的下午,戴住了他翻墙回来时额角的汗水,戴住了第一次心动时手心的温度。
大二那年冬天,他坐二十多个小时的硬座来看我。在火车站,他看见我头发上别的已经不是那个发夹,眼神暗了一下。我没解释,只是从包里掏出旧发夹给他看——我用丝绒布包着,放在一个小铁盒里。
“太旧了,怕戴坏了。”我说。
他摸摸我的头,说傻瓜。
那时候真以为会一直这样下去。年轻时的爱情总让人觉得,只要心意够坚定,什么距离、时间,都不是问题。
可后来啊,我们还是走散了。没什么狗血剧情,就是慢慢地,电话少了,共同话题没了,最后连“分手”都没正式说,就默契地不再联系。
收拾他寄回来的东西时,我哭了整整一夜。所有他送我的礼物里,我只留下了那个发夹。其他的都扔了,或者送人了,唯独这个发夹,我把它放回那个小铁盒,塞在衣柜最深处。
毕业后工作、搬家,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。每次整理东西都会看见那个铁盒,但很少打开。发夹的颜色更淡了,塑料有点发脆,我不敢再碰,怕一碰就碎了。
2018年,我从北京搬去杭州。打包的时候特意把铁盒放在随身行李里,可到杭州打开箱子,怎么也找不到了。我把所有行李翻了三遍,给搬家公司打了无数电话,最后不得不承认——它真的丢了。
那一刻我坐在新家的地板上,周围全是没拆的纸箱,突然就哭了。不是嚎啕大哭,就是眼泪止不住地流。我才意识到,我哭的不是失去了他,也不是失去了青春,而是失去了一个实实在在的、可以触摸的凭证。
那个发夹见证过我最纯粹的心动,承载过最笨拙的深情。它不值钱,也不起眼,可它是我十六岁全部心事的容器。握在手里,就能回到那个消毒水弥漫的春天,回到他满头大汗递给我礼物的瞬间。
现在,连这个容器也没有了。
去年高中同学聚会,他来了。我们都三十多了,他发际线后移了些,我也早就不扎马尾。聊起近况,他妻子刚生了二胎,我女儿今年上小学。说起高中趣事,有人提起他翻墙买发夹的事,大家哄笑。
他看着我,眼神温和:“你还留着吗?”
我摇摇头:“搬了好几次家,弄丢了。”
他笑笑:“可惜了。”
其实不可惜。我后来明白,有些东西注定是要消失的。就像那个发夹,就像我们年轻时的爱情。它们存在过,美好过,就够了。
前几天整理女儿的东西,发现她也有个类似的发夹,粉色的,塑料的。她嫌旧了,不想戴了。我拿在手里看了很久,突然想起他送我的那个。
原来每个女孩都会在某个年纪,收到这样一个发夹。它普通,却独一无二;它廉价,却无价。它会被弄丢,会被遗忘,但曾经别在发间时的那种悸动,会留在记忆里,永远崭新。
那个淡紫色的蝴蝶发夹,早就找不到了。可我记得它别在刘海旁的重量,记得它勾住头发时轻微的疼痛,记得它在阳光下的颜色。这些记忆,比发夹本身更牢固地别在了我的生命里。
就像他,就像十六岁的春天,就像所有逝去的美好——它们不在任何地方,因为它们无处不在。在每一个相似的瞬间,在每一次心动的回响里,它们都会悄然浮现,提醒我曾经那样热烈地活过,爱过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品易文章网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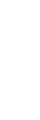 品易文章网
品易文章网
热门排行
阅读 (131)
1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21)
2扫码领洗发水,收到后是小瓶装阅读 (119)
3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9)
4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17)
5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