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些书还带着印刷厂的温度,封面光滑,书页紧密。它们即将被编入系统,贴上标签,成为这座百年老馆的一部分。我的任务,就是完成它们“出生”后的第一道手续——新书入库登记。
翻开第一本书的扉页,我愣住了。这是一本关于民间工艺的图册,出版日期是去年冬天。而在版权页的角落,有人用铅笔轻轻写着:“给未来的读者——愿手艺不灭。”
我的手指抚过那行小字。这本书从作者写下最后一个字,到编辑审校,再到印刷装订,经历了多少人的手?而现在,它来到了我这里。我突然意识到,自己正在参与的,不只是简单的工作流程,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交接。
我拿起印章,蘸上红色印泥,在指定位置轻轻压下。“XX图书馆藏”——六个字清晰地印在书页上。这个动作,图书馆员们重复了上百年。从木刻印章到钢印,再到现在的光敏印章,工具在变,但这个仪式的本质从未改变:一本书从此有了归宿。
接着是贴条形码和RFID芯片。我把拇指大小的芯片贴在书脊内侧,像给新生儿戴上身份牌。以后,这本书在架上的位置、被谁借阅、何时归还,都将被这个小小的芯片记录。现代技术让管理变得更高效,但我更愿意相信,这是在为每本书建立独一无二的生命轨迹。
盖完章的书需要分类。我按照中图法,开始在书脊上贴标签。《民间工艺图录》属于艺术类,J开头。我小心地写着编号,生怕写错一个数字,就会让这本书在茫茫书海中迷失方向。
最让我动容的是处理一批捐赠的旧书。其中一本《诗经选读》的扉页上,有人用钢笔工整地写着:“购于1985年9月,北京。”书页间夹着一片早已干枯的银杏叶,叶脉如细密的蛛网。我犹豫了一下,没有把它取出——这是属于这本书的记忆,应该让它随书流传。
还有一本《小王子》,内页用彩笔画满了星星和绵羊。在“如果你驯养了我,我们就会需要彼此”这句话下面,画着一个小小的箭头,指向页边歪歪扭扭的字:“我想被驯养。”我的心突然柔软起来。这些看似不该出现在书上的“涂鸦”,恰恰是书与人之间最真实的联结。
那天下午,当我为最后一本书贴上标签时,夕阳正透过高窗洒进书库。光线中有尘埃缓缓飘浮,像是无数故事在空气中舞蹈。我站直身子,看着桌上整理好的新书——它们不再是一摞待处理的物品,而是一个个等待开启的生命。
我想起自己小时候,总是好奇图书馆的书从哪里来。现在我知道了,每一本在架上等待被借阅的书,都经历过这样的旅程:从出版社到图书馆,经过一双双手,被盖上印章,贴上标签,然后静静等待与某个读者的相遇。
完成登记的新书被送上推车,准备进入流通系统。我推着车走在长长的走廊里,轮子与地面摩擦发出规律的声响。明天,这些书就会被摆上书架,开始它们真正的使命——被翻阅,被阅读,被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空里理解。
回到书库,我拿起那本《民间工艺图录》,再次翻开扉页。除了我盖上的红印,那行“给未来的读者”依然清晰。我找来铅笔,在下面添上一句:“手艺不灭,因为有人传承。——图书管理员,2023年春”
合上书,我忽然明白,我们这些做图书管理员的,何尝不也是另一种手艺人?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书,更是书与人之缘。每一本经过我们手的书,都可能在某一天改变某个人的生命轨迹。就像多年前,我在图书馆偶然抽出的那本《梵高传》,让我从此爱上了艺术。
夜幕降临,我锁上书库的门。身后,成千上万册书在黑暗中静静呼吸,等待下一个黎明,等待下一双翻开它们的手。而我知道,明天还会有新书到来,还会有新的故事等待被登记,被珍藏,被传递。
这份工作教会我的,远不止如何分类编目。它让我懂得,每一本书都是有生命的。而我们,是这些生命旅程中的驿站管理员,负责把它们安全地送往下一个目的地。当有一天,你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抽出一本书,看到扉页上那枚红色的印章,或许会想起——曾经有人,如此郑重地迎接过它的到来。
这就是我的工作,平凡,却连接着无数可能的相遇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品易文章网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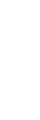 品易文章网
品易文章网
热门排行
阅读 (131)
1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21)
2扫码领洗发水,收到后是小瓶装阅读 (119)
3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9)
4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17)
5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