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盖上空荡荡的箱子,听着那熟悉的、因为融化而滴滴答答的声响终于停了,反倒觉得周围一下子过于安静了。一百支,一支不多,一支不少,今天就卖完了。这心里头,一下子空落落的,像是完成了一件什么了不得的大事,又像是失去了一个天天见面的老朋友。
这批老冰棍,还是天刚蒙蒙亮那会儿,我从老陈的批发部蹬着三轮车拉回来的。那时候街上还没什么人,风也带着点儿凉气。老陈跟我是老交情了,一边帮我搬箱子,一边用毛巾擦着脖子上的汗,笑着说:“老哥,今天又是好天儿,你这‘硬通货’肯定走得快。”箱子沉甸甸的,白色的冰棍整整齐齐地码在里面,隔着纸箱都能感到那股子凉意。我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放进我的泡沫保温箱,四周再塞上厚厚的棉垫子,像安顿一群怕热的孩子。
我的摊子就支在街角的老槐树下,这树有些年头了,枝叶茂密,能遮住大半天的日头。上午八九点钟,太阳开始发威,第一批主顾就来了。多是些赶早市回来的大爷大妈,手里拎着新鲜的蔬菜。他们不像年轻人那样追求花里胡哨的雪糕,就认这个老味道。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,慢慢走过来,递过一张皱巴巴的一块钱:“还是老样子,一支老冰棍。”我递给她,她接过去,并不急着吃,只是拿在手里,眯着眼端详那简单的包装,喃喃道:“还是这个样儿,跟我小时候一分钱一支的时候,没啥大变化。”她就那么站在树荫下,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,那神情,不像是在吃冰棍,倒像是在品味一段遥远的、甜丝丝的旧时光。看着她,我心里也暖暖的。
到了中午,那是真叫一个“战况激烈”。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天上,晒得人皮肤发烫。放学的孩子们像一群小麻雀,呼啦啦地围过来,举着零花钱,叽叽喳喳地喊着:“我要老冰棍!”“我也要!”他们拿到手,迫不及待地撕开,往往因为太心急,会把包装纸撕破,黏糊糊的糖水沾一手。他们才不在乎,大口大口地咬着,冰渣子沾在嘴角、鼻尖上,笑得没心没肺。有个胖乎乎的小男孩,几乎每天中午都来,每次都买两支,一手拿一支,左边咬一口,右边舔一下,那满足劲儿,仿佛拥有了全世界。看着他们,我就想起我儿子小时候,也是这副馋样。这小小的冰棍,承载了多少孩子最简单、最直接的快乐啊。
下午两三点,是一天里最熬人的时候。街上行人稀少,连知了都叫得有气无力。这时候来的,多是些为生活奔波的苦命人。外卖小哥把电瓶车往树下一靠,头盔都来不及摘,满头满脸的汗,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。他扫码付钱,接过冰棍,常常是三五口就解决掉一支,那冰凉的甜水顺着喉咙下去,仿佛能瞬间浇灭五脏六腑里的火。他会长长地舒一口气,对我说:“老板,还是你这老冰棍解渴,顶事儿!”还有那浑身沾满油漆点子的装修工人,穿着被汗水浸透的工服,靠在墙角,默默地吃着一支冰棍。那一刻,他没有说话,只是安静地享受着这片刻的清凉和休息。这支普普通通的冰棍,对于他们而言,不是消遣,是救急的甘霖,是喘口气的安慰。
傍晚,热气稍稍退去,出来散步的人多了。保温箱里的冰棍也所剩无几了。这时候的买卖,节奏慢了下来。会有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来,爸爸往往会对孩子说:“来,尝尝爸爸小时候吃的冰棍是什么味儿。”孩子咬一口,可能会皱皱眉:“没有巧克力呀?”爸爸就会笑着解释:“这才是最原来的味道。”我看着他们,心里想,这味道,大概就是这样,一代一代,在不经意间传下去的吧。
现在,箱子彻底空了。我拿起一支掉在箱底的、断成两截的冰棍,它已经化得不成样子,软塌塌的。我把它放进嘴里,那股熟悉的甜,带着点儿淡淡的奶香(或者说是麦香?),在舌尖上慢慢化开。就是这个味儿,几十年都没变。它不复杂,不惊艳,但就是那么实在,那么妥帖。
这一百支冰棍,就像一百个小小的故事。它们被不同的人买走,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地点,慰藉着不同的人生。它们见证了一个卖冰棍的老头平凡的一天,也参与了许多陌生人或忙碌、或悠闲、或艰辛、或甜蜜的生活片段。这支小小的冰棍,像一根看不见的线,把我和这条街,和这些来来往往的人,轻轻地联系在了一起。
明天,天不亮我又得去老陈那儿进货了。保温箱还会被填满,还会有一百支老冰棍,静静地等着,去遇见新的面孔,去滋润新的焦渴。日子,就是这样,在一次次清空与填满之间,慢慢地流淌着,简单,却又有它自己的分量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品易文章网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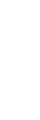 品易文章网
品易文章网
热门排行
阅读 (131)
1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21)
2扫码领洗发水,收到后是小瓶装阅读 (119)
3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9)
4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17)
5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