头一个月,我们几个骨干几乎住在了实验室。白天调试、测试、失败;晚上开会、争吵、再定新方案。我们把能想到的传统方法和一些前沿思路都试了个遍,电路板改了一版又一版,代码堆得像小山,但每次满怀希望地启动设备,屏幕上那跳动的、不稳定的波形图,都像在无情地嘲笑着我们的努力。那面用来写思路的白板,被各种颜色的笔画得密密麻麻,又一次次被擦掉,最后连板子本身都泛着一种擦不干净的灰白色。团队的士气,也从最初的火热,慢慢降到了冰点。有人开始沉默,有人忍不住抱怨,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精疲力尽的焦虑。我记得最清楚的是,有一天凌晨三点,我又一次看着测试数据发呆,旁边的老李,一个干了十几年研发的硬汉,突然把手中的万用表往桌上一扔,哑着嗓子说:“没招了,真的没招了。这东西,是不是根本就做不到?”
他这句话,像根针一样扎在我心里。我知道,不能这么下去了。蛮干,只会耗尽最后一点元气。那天晚上,我给自己泡了杯浓得发黑的咖啡,坐在电脑前,做了一个看似笨拙,却可能是唯一正确的决定:回归基础,系统地、大规模地查阅文献。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,不看完200篇相关领域的中外文献,绝不再轻易动手做实验。
接下来的日子,我进入了一种近乎封闭的状态。办公室、图书馆、宿舍,三点一线。我的办公桌被打印出来的论文堆满了,中英文的都有,分门别类,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标签。上午,我集中看国内高校和研究所的最新成果;下午,主要攻克IEEE上的那些英文论文;晚上,则是对比、梳理、做笔记。
这个过程,枯燥至极,但也时有惊喜。大部分论文看下来,可能只觉得“哦,原来他们是这么做的”,但对我们面临的问题没有直接帮助。可你不能急。就像在沙滩上淘金,大部分是沙子,但总能在不经意间,发现一两点闪光的金屑。
我记得,那大概是在我翻阅到第130多篇文献的时候,那是一篇来自欧洲一个不太知名实验室的论文,他们研究的方向和我们并不完全一致,但文中提到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信号处理算法,用来解决另一种类型的干扰。我当时脑子里“叮”了一下,像是有个灯泡被点亮了。我立刻把这篇文献做了重点标记,然后顺着这个思路,去查找它引用的,以及引用它的其他文章。
这个线索,像一根线头,扯出了一大片新的天地。我发现在另一个看似不相关的学科领域——医学影像处理里,为了解决图像噪点问题,他们发展出了一套非常复杂的多维度滤波和重构技术。我把这个发现和团队分享,起初大家都觉得有点“脑洞大开”,跨领域太大了。但我们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,开始尝试将这套理论的核心理念,“翻译”成我们通信领域的语言。
这又是一个痛苦磨合的过程。理论是别人的,工具是我们的。我们不断地讨论、建模、仿真,把医学影像里的“像素”对应成我们的“数据包”,把“图像噪点”对应成“信道干扰”。那段时间,实验室里又恢复了生气,虽然还是经常争得面红耳赤,但大家的眼睛里,重新有了光。我们知道,我们可能摸到门了。
在目标期限前的最后半个月,我们整合了从各个文献中汲取的灵感,尤其是那个医学影像算法的核心思想,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,提出了一套全新的、混合式的信号处理架构。当我们在仿真软件里跑通第一个模型,看到那条几乎完美的、平滑稳定的信号曲线出现在屏幕上时,整个实验室安静了几秒钟,然后爆发出了一阵欢呼。老李冲过来,狠狠地拍着我的肩膀,眼眶有点红。
后续的实物测试虽然也遇到了一些波折,但大的方向已经打通,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。当最终的测试报告出来,所有指标不仅达标,甚至部分还超出了预期时,我一个人走到实验室外面的天台,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三个月的煎熬,两百多篇文献的积淀,无数个不眠之夜,在这一刻,都值了。
现在,每当有年轻的同事遇到看起来无法逾越的技术难关,来向我请教“秘诀”时,我总会跟他们讲起这三个月的故事。我告诉他们,没有什么捷径和奇迹,所谓的“灵光一现”,其实都建立在大量、扎实、甚至略显笨拙的积累之上。当你感到山穷水尽的时候,不妨静下心来,回到知识的海洋里,像淘金一样,耐心地去寻找那些可能照亮前路的“金屑”。那两百篇文献,不仅帮我攻克了那个具体的技术瓶颈,更在我心里筑起了一座坚实的知识堡垒,让我在面对任何新的挑战时,都多了一份底气和从容。这条路,走得很慢,很苦,但每一步,都算数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品易文章网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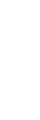 品易文章网
品易文章网
热门排行
阅读 (131)
1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21)
2扫码领洗发水,收到后是小瓶装阅读 (119)
3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9)
4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17)
5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