厨房传来煎蛋的滋滋声。
这是我们婚姻里关于周末懒觉的最初模式:他早起,我赖床,互不打扰。
他是个生物钟极准的人,雷打不动七点醒。而我,能把周末过得像时差倒错——周五熬夜追剧,周六一觉睡到十点半。起初这没什么,甚至觉得挺好。他轻手轻脚起床,带上门,在客厅看书,或者准备一顿丰盛的早午餐。我则在卧室里,拥有一个无人打扰、可以肆意翻滚的回笼觉。
我们像两个配合默契的室友,在周末的上午,各自占领一块领地,井水不犯河水。
他会在我终于揉着眼睛走出卧室时,从报纸后抬起头,笑着说:“小猪起床了?”然后去热牛奶,烤面包。我则会夸张地吸着鼻子,说:“哇,好香啊,先生真能干。”这种模式,维持了大概一年。客气,体贴,但总感觉中间隔着一层薄薄的、凉凉的什么。
第一次打破这种平衡,是一个冬天的周六。
前一天晚上,我们为一件现在完全想不起来的小事争执了几句。不算吵架,就是心里都憋着点不痛快,背对背睡着了。第二天我醒来时,才八点多。意外地发现,他居然还在睡,而且面向我这边,呼吸均匀。
屋子里静悄悄的。那点不痛快还在心里堵着。我打算像往常一样,等他先起。可等了十分钟,他毫无动静。我无聊地开始数他的睫毛,研究他额头上新冒出的那颗痘。看着看着,心里那点气,莫名其妙就消了一半。
就在这时,他忽然动了动,眼睛没睁开,手臂却下意识地往我这边捞了一下,正好搭在我腰上。然后,他好像终于醒了,睁开眼,我们对视了。空气有点凝固。我以为他会立刻把手收回去,恢复那种礼貌的距离。
但他没有。他只是眨了眨眼,含糊地问:“几点了?”
“还早,”我说,“再睡会儿吧。”
“嗯。”他应了一声,那只手非但没拿走,反而收紧了些,把我往他怀里带了带,然后再次闭上眼睛。
我的身体先是微微一僵。结婚以来,我们很少在醒着的时候,这样无所事事地仅仅抱着。拥抱似乎总是有目的的——睡前仪式,或者亲密的前奏。像这样,在清晨的懵懂里,单纯地贴着,是第一次。
我的额头抵着他的下巴,能感受到他温热的呼吸拂过我的发顶。他的心跳隔着睡衣,一下,一下,沉稳地传过来。昨晚那点残存的不愉快,就在这心跳声里,彻底融化掉了。谁也没有再提。
我们就这样,听着窗外偶尔响起的鸟叫和远处模糊的车流声,迷迷糊糊地,又睡了一个回笼觉。直到快十点,才一起饿醒。
那个上午,感觉和以往任何一个周末都不同。没有谁特意做饭,我们一起钻进厨房,他煎蛋,我热牛奶,胳膊肘时不时撞到一起,相视一笑。阳光洒满了半个客厅,亮堂堂的。
从那以后,我们的周末懒觉,开始悄悄变味了。
不再是绝对的“互不打扰”。有时,我会在他轻手轻脚准备下床时,闭着眼睛嘟囔一句:“再躺五分钟嘛……”他犹豫一下,真的会躺回来。那五分钟,我们往往也睡不着,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。说说做的梦,或者计划一会儿去哪家新开的店尝尝。
有时,是他破天荒地赖床。我会先醒,但不再急着起来,而是看着他睡。看他像个孩子一样把半张脸埋进枕头,看他的头发睡得翘起一撮。看着看着,心里会涌起一种很柔软的满足感。
当然,这个过程并非总是温情脉脉。
有一次,我感冒了,鼻子不通气,夜里醒了好几次。周末早上,他照例先醒了,看我睡得沉,就没动。结果我一个翻身,把一条腿毫不客气地压在了他身上,还因为呼吸不畅,打起了小呼噜。我能感觉到他身体瞬间的僵硬,但他还是没有推开我,只是轻轻调整了一下姿势,让我枕得更舒服点,然后拿起床头的手机默默地看。等我彻底睡醒,已经快中午了。他半边身子都被我压麻了,一边龇牙咧嘴地活动胳膊,一边开玩笑说:“你这呼噜打得,跟个小发动机似的。”
我有点不好意思,他却凑过来,用额头贴了贴我的额头,说:“嗯,好像不烧了。”
那一刻,我觉得所谓婚姻,可能就是连自己最不设防、最不优雅的样子,也可以安心地暴露在对方面前,而对方只是担心你烧不烧。
我们一起睡的“技术细节”,也是在无数次磨合中完善的。
比如抢被子。我睡相不好,夏天还好,一到冬天,就像个卷铺盖能手,经常把他冻醒。后来,我们干脆换了一床超大尺寸的双人被,问题迎刃而解。
还有枕头的高度。他喜欢矮的,我喜欢高的。最终解决方案是,我们买了两个不同高度的枕头,并排放着。睡到半夜,有时我们会下意识地寻找最舒服的位置,最后常常变成共享一个枕头,头靠着头。
最有趣的是起床气。他没有,我有。如果我没睡饱被强行叫醒,会一上午脸色阴沉。他发现了这个规律后,再也不在我睡着时接任何吵人的电话,如果快递或者外卖来了,他总是第一时间冲出去,把门轻轻掩上,在门外完成交接,再像做贼一样溜回来。
这些小动作,这些不言不语的默契,比任何甜言蜜语都让我觉得踏实。
现在,我们的周末通常是这样的:
不再有固定的谁先醒谁后醒。有时是他先醒,玩一会儿手机,然后放下手机,看着我,看着看着,会凑过来亲一下我的额头或脸颊,把我弄醒。我哼唧着表示抗议,他却笑了,说:“走,起床,带你去吃你念叨了一周的生煎包。”美食的诱惑总是巨大,我通常会一边抱怨一边爬起来。
有时是我先醒。我会坏心眼地用手指轻轻描他的眉毛,或者往他耳朵里吹气。他会闭着眼笑,一把将我搂住,说:“别闹,再抱十分钟。”这十分钟,往往安静而绵长。我们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和心跳,能感受到被子里的温度一点点升高。什么都可以想,什么都可以不想,只觉得时间好像慢了下来,外面世界的喧嚣都与我们无关。
我们从两张床,到一间卧室;从互不打扰的默契,到肢体纠缠的亲昵;从客气地分享空间,到自然地分享睡眠。这个过程,不是刻意经营出来的,它就像植物生长,自然而然。
现在,我依然会偶尔怀念最初那个可以独占大床、睡到天昏地暗的周末。但相比之下,我更迷恋现在这种——在半梦半醒间,能感觉到身边另一个人的体温;在翻身时,手臂会碰到他的身体;在做噩梦惊醒的瞬间,能听到他平稳的呼吸声,于是再次安心睡去。
这大概就是婚姻赋予懒觉的另一种意义。它不再是一个人的充电和放空,而是两个人的依靠与共生。我们在这张小小的床上,分享着最不设防的时光,也修复着一周生活带来的细微磨损。
窗外,邻居家传来炒菜的香味,又一个中午要到了。他动了动,终于决定起床。他坐起来,伸了个大大的懒腰,骨骼发出轻微的响声。然后他回过头,看着还蜷缩在被子里的我,眼睛弯起来:
“懒猪,太阳晒屁股啦。想吃什么?我去做。”
我把脸埋进还留着他体温的枕头里,闷声说:“随便,你做的都行。”
听着他趿拉着拖鞋走出卧室的声音,厨房里很快传来烧水、准备锅具的熟悉响动。我知道,再过一会儿,房间里就会飘满食物的香气。而我,将拥有这最后几分钟,独属于我的,但又与他紧密相连的懒觉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品易文章网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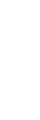 品易文章网
品易文章网
热门排行
阅读 (131)
1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21)
2扫码领洗发水,收到后是小瓶装阅读 (119)
3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9)
4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17)
5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