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和小敏结婚那天种的它。记得特别清楚,那是四月的一个周末,前一天刚下过雨,泥土还湿漉漉的。婚礼简单办完,第二天睡到自然醒,两个人穿着睡衣就开始折腾这棵树。是我从苗圃挑的,一棵香樟,听说这种树活得久,能长好几百年。
“挖深点,”小敏蹲在旁边,用手比划着,“太浅了怕站不稳。”她总比我细心。
我吭哧吭哧地挖坑,汗顺着额头往下淌。小敏就捧着树苗,轻轻理着它的根须。那树苗真小啊,细细的杆子,还没我胳膊粗,叶子稀稀疏疏的几片,风一吹就抖个不停。
“它能活吗?”我有点担心。
小敏笑了,露出两个酒窝:“咱俩一起种,肯定能活。”
埋好土,我们轮流去井边打水。小敏非要提半桶,摇摇晃晃地走回来,水洒了一路。浇完水,她在树干齐腰的地方系了根红绳,说这是记号,等树长高了,就知道当初它有多矮。
“等咱们老了,”她靠着我的肩膀,“这树应该能遮阴了吧?”
那时候觉得“老了”是特别遥远的事。
头三年,我们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它。春天怕倒春寒冻着,我用旧衣服给它做了个“围脖”;夏天太阳毒,小敏找了块纱布给它遮阴;生了虫子,两个人蹲在树下一只一只地捉。每年结婚纪念日,我们都会在树下拍张照——第一年,树才到我腰间;第三年,已经超过我的肩膀了。
有一年闹虫害,叶子被啃得七零八落。小敏急得直跺脚,大中午的顶着太阳去农资店买药。喷药的时候,她不小心吸进去一点,咳嗽了半天。我怪她太着急,她却说:“再不治,树就要死了。”那天晚上,她每隔一会儿就要打手电筒去看看。
树慢慢长大,我们的生活也在变。第四年,我换了工作,经常加班到很晚。每次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,看见院里的树黑黢黢的轮廓,心里就会踏实些——家里有盏灯,树下有个人在等我。
小敏习惯在树下等我。夏天搬个小马扎,摇着蒲扇;冬天就站在树旁跺脚取暖。看见我回来了,她会小跑着过来,树影在她身上明明暗暗地闪过。
“吃饭了吗?”永远是这句话。
有时我心情不好,她就拉我到树下坐坐。“你看,”她指着树说,“今年又长高了一截。”是啊,树在长,我们的生活也在继续。再难的事,好像看看这棵树,就觉得还能坚持下去。
第七年,树已经高过房檐了。春天会开细细碎碎的花,淡黄色的,风一吹,香味能飘进屋里。夏天,树荫能罩住半个院子,我们终于在树下摆了石桌石凳,实现了当初“在树下乘凉”的愿望。
也就是那年,小敏怀了孩子。她孕吐严重的时候,就坐在树下深呼吸,说树的味道让她好受些。后来肚子大了,她扶着腰站在树下比划:“等孩子出生,树荫应该能盖住整个石桌了吧?”
女儿出生在秋天,树开始落叶的季节。从医院回家的第一天,我推着婴儿车走进院子,发现小敏正抱着女儿在树下转悠。
“来,认识一下咱们家的成员。”她轻声对女儿说,然后抬头看看树,“这是咱们一起种的,以后你也要照顾它哦。”
那天阳光很好,透过枝叶缝隙洒下来,在女儿粉嫩的小脸上跳跃。我突然觉得,这就是家的样子——有树,有人,有生生不息的希望。
孩子会爬了,在树荫下玩玩具;会走了,摇摇晃晃地追落叶;会说话了,第一句完整的话是“树树高高”。我们在树下给她过生日,教她认树叶,告诉她这棵树和咱们家一样,都是一点点长大的。
现在,女儿已经会抱着树干转圈了,小敏的眼角有了细纹,我的鬓边也见了白发。只有树还在不停地长,比二层楼还高,树冠郁郁葱葱的。麻雀在枝杈间做窝,夏天知了吵得人睡不着。
上个月刮台风,树枝被刮断了好几根。雨停后,我和小敏一起收拾残局。她捡起一根断枝,看了很久:“时间过得真快啊。”
是啊,真快。当初种树的时候,我们还是两个毛头孩子,现在女儿都会打酱油了。这棵树见证了我们所有的日子——吵架后我在树下抽的闷烟,她生气时踢树一脚(轻轻的),女儿第一次走路时我们的欢呼,还有无数个平常的夜晚,一家三口在树下吃西瓜、数星星。
昨天傍晚,我们又在树下乘凉。女儿和邻居小孩追逐嬉戏,小敏低头剥着毛豆,我靠在椅背上,看夕阳把树影拉得老长。
“要是能一直这样就好了。”小敏突然说。
我没接话,只是伸手握住了她的手。树在风里沙沙作响,像是听懂了,又像是在回应。
这棵树啊,它不只是树。它是我们的时光机,每一圈年轮里都藏着一段故事;它是我们的定心丸,再难的日子,看看它还在长,就觉得生活还有希望;它更是我们的见证人,看着两个年轻人怎样一步步变成父母,怎样把爱情过成了亲情。
夜深了,我起身关窗,最后看了眼月光下的树影。明天太阳升起时,它还会在那里,和我们一起,迎接新的日子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品易文章网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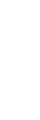 品易文章网
品易文章网
热门排行
阅读 (131)
1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21)
2扫码领洗发水,收到后是小瓶装阅读 (120)
3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19)
4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7)
5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